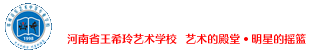戏曲现代戏创作回顾与反思

我是1963年开始接触戏曲现代戏创作的,那时我刚刚从原中国戏曲学院(1958—1963)导演专业毕业,被分配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工作。工作伊始正赶上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剧团成立,于是被安排到实验剧团跟随我的老师李紫贵先生继续学习。这里有个小插曲,所谓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剧团,就是由当时的中国京剧院三团整个建制搬过来的,那为什么不叫实验京剧团而叫实验剧团呢?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周扬传达指示说,实验剧团就是要搞实验,搞实验就有可能搞出个非驴非马的东西来,非驴非马不可怕,非驴非马那就是骡子嘛!剧团成立之时恰逢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前夕,为了参加大会,决定创作两出戏,一出是《红旗谱》,另一出是移植自当时著名的同名豫剧现代戏的《朝阳沟》。
《红旗谱》的编剧是当时学院的晏甬院长和吴琼老师,以及学院文学班毕业实习的苏明慈;音乐设计是学院的舒模老师和乔东君老师,以及学院音乐班毕业实习的安志强;舞美设计是当时人称“老夫子”的张正宇先生和他的助手陈永祥老师;灯光设计是苏丹老师;导演是李紫贵先生,我跟着老师做场记。戏的二度创作是从体验生活开始的,1963年的年底我们来到高蠡暴动的发生地高阳,一住就是81天,在那里过的春节。当时紫贵先生提出的要求是:通过体验生活,首先演员要像农民,然后要像“这一个”农民,最后再过渡到戏曲舞台上的人物形象。紫贵先生指导剧组做了三件事情:一是采风,剧组住过农民的家里,当时正赶上高阳大水之后,市面上有些萧条,特别是春节前的集市氛围给了大家很多启发,一下子就让我们从农民的外部形象和气质上找到了感觉。二是做生活小品,让演员逐渐向人物靠拢,比如朱秉谦扮演的老驴头从生活中借鉴了许多细节,用到小品里就显得非常生动;其他角色如袁国林的朱老忠、任凤坡的朱老明、王荣增的冯老兰等,都从生活和小品创作中得到了许多启迪。我也做过小品,是和李春城一起,他演贾湘农,我演江涛,遗憾的是我不是演员出身没能完成任务,最后还是请赵寿延承担了江涛这一角色。三是强化音乐的作用,用音乐规范人物的形体动作和心理节奏,规范群众场面的处理。第一场朱老忠站在大堤上,姿态有了,神气有了,导板头的锣鼓和胡琴一响,演员身上的京剧感觉立马就出来了。再有序幕里表现春节前萧条的集市景象,有卖菜的、算卦的、挑着对联串街走巷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生活气息很是鲜活,当衬曲把这一切镶在曲子里响起的时候,所有调度和吆喝声都变得有次第、有节奏了。接着一声鞭响,伴唱声起:“红呢轿车响一鞭,村村镇镇愁云添。”接着起快长锤锣鼓点,冯贵堂穿场走过,原本散漫节奏里的生活景象刹那间充满了浓郁的戏曲味道。这出戏的唱腔设计也很有意思,特别体现在花脸的有些唱段,先是由老师们提出构想,然后请剧团里能哼腔的花脸演员李欣具体哼唱,一遍一遍地试,合适了才记下来。当时的李欣很年轻,每次编腔时老师们都会开玩笑说,编好了奖励一斤粮票,可见当时的创作氛围是很宽松、很愉快的。后来这出戏在当时的中国戏曲学校排演场彩排时,许多京剧界的前辈,如萧长华老先生看了都很满意。遗憾的是,由于政治原因,《红旗谱》没有能上演。
实验剧团的另一出戏《朝阳沟》,剧组全体在北京山区斋堂体验生活,先学习豫剧《朝阳沟》,然后再移植成京剧。这个戏的导演是刘木铎老师,由刘秀荣、张春孝和王梦云老师主演,大家下了很大的功夫,但终究没达到像豫剧原作那样的效果。后来仔细琢磨,不同剧种之间是有差别的,京剧的审美气质和豫剧的那种乡土气息之间是有些距离的,不同剧种在题材选择上各有自己的优长和局限,不能觉得在其他剧种成功的剧目,特别是那些生活气息和戏剧情趣浓郁的剧目,京剧拿过来改一改就能获得同样的演出效果。
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剧团准备参加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两出剧目都没有被选定,所以就从演出团变成了观摩团,但还是从头至尾观摩了整个会演的剧目,也参加了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的接见。那时的会演不是演完就走的,都是全程参加的,包括观摩团在内。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有幸在阿甲先生排完京剧《红灯记》第四场,也就是“痛说革命家史”一场后,去人民剧场观摩学习了这出后来成为“样板戏”的优秀剧目。当时的感觉是,阿甲先生排的戏和我的老师李紫贵先生排的戏,确有不同的特点,阿甲先生的戏在程式的运用上很是讲究和严谨,而紫贵先生在运用程式的时候则是更加注重对于生活形态的体验。观摩两位先生排出来的戏还是能辨认出来不同风格的,这与二位先生对戏曲中程式与生活、技巧与体验,这对既矛盾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各有侧重有关系,当然也与二位先生各自的艺术经历分不开。
后来实验剧团又排了京剧《昆仑山上一棵草》,这是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一个剧目,由苏一平先生和刘武先生编剧,刘吉典先生的唱腔和音乐设计,主演是高玉倩老师及刘长瑜、李长春、李光等,由李紫贵先生导演,我还是跟着老师学习。《昆仑山上一棵草》写的是有关青藏公路上兵站的故事,所以全体主创人员,除高玉倩老师有高血压留在格尔木外,其他老师一共13人全都乘汽车走青藏公路到海拔4800米的昆仑山上去体验生活,记得后来主抓这出戏的林默涵副部长和此前担任过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苏一平先生也亲自去了一趟西北采风。戏也是从小品开始进入二度创造的,记得为了设计唱腔,刘吉典先生和编剧就唱词还有过讨论,吉典先生认为有些唱词的格律不太合适,希望作者能改一下,他当时说:“这样的词不是我不能编,你给我一张《人民日报》我也能都给你唱下来,可这不是那么回事。”如今回想起来,刘吉典先生的音容笑貌仍在面前,我们是同乡,先生那略带天津味儿的口音十分亲切。彩排是在当时的芭蕾舞团排演场进行的,之后很快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出戏也因此撂下了。实验剧团存在的几年里,任桂林,还有吴祖光等先生们都曾参与过剧团的创作,比如编排了《战斗的南方》等时令戏,但很可惜都没能留下来,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实验剧团被撤销又回到了中国京剧院。
“文化大革命”中我虽然没有参加戏曲的创作活动,但有一件事对我认识戏曲现代戏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那就是从“干校”回来以后,我被派到北京京剧团去帮忙总结《杜鹃山》创作经验的一段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经验”中的有些提法对戏曲现代戏的创作还是有一些实践作用的,比如“四性”的提法:“念白的音乐性,身段动作的舞蹈性,群众场面的规范性,舞台节奏的统一性。”为什么提出这“四性”,又如何实现这“四性”呢?“经验”中就特别强调了“音乐笼罩”和对全剧的“渗透”作用,因为有了音乐的笼罩和渗透,它的语言和形体动作就要发生变化,就要适应音乐的节奏和韵律,我们翻一翻《杜鹃山》的音乐总谱就会发现,人物演唱中的动作,甚至一些动作细节,都清清楚楚地标注在乐谱上。“经验”中还包括对群众场面的规范要求:“聚要聚的拢,散要散的开”,“聚散有形”是为了适应音乐而铺排的。这些要求对于戏曲舞台上如何表现现代生活、如何实现戏曲舞台歌舞化的形态特征都有着方法论上的意义。在“经验”中,也有许多对技巧和技法的概括,比如:对武打的要求,要“打出情节、打出人物、打出地貌”;重要的舞台处理一定要做好铺垫,不仅要有“近铺垫”,还要有“远铺垫”;还有戏曲演出结构中“重复再现”手法的使用,记得为了说明戏曲的这一特点,剧团还专门排了一出小戏予以实证,这实际上就是强调戏曲整体把握的问题。另外,对导演的工作程序,也提出了“有主导地综合整体,分阶段地统一进行”的方法,以避免打乱仗、乱打仗的情况等。这些经验总结虽然还没有更加深入戏曲的美学精神层面,但在当时的创作背景下,也还是具有一定实践价值的。当时在音乐设计上的许多创新经验,如借鉴歌剧的主导动机的介入手法发展出来的主题音乐,人物的特性音调等,大大丰富了导演的表现手段,不仅在舞台气氛烘托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上更为强化,而且在提升和展示一出戏的精神意蕴上给了导演很大的帮助。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参加导演的一些戏,如京剧《石龙湾》、上党梆子《陈圆圆》等都在这方面留有一定的痕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逐渐感觉到一些问题,那就是戏排出来虽比较精致细腻,但有时又过于拘谨而不够灵动,这些问题,特别是在那些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剧种身上显得尤为突出。虽然都是以歌舞演故事,但是对生活提炼的程度却不尽相同,有的形态离生活原生态近一些,有的远一些,特别是对一些生活化程度高、程式规范不像京剧那么严谨的剧种,恐怕在歌舞化的理解和把握上就不能那么机械拘谨,该严则严,该松则松,戏的流动才会更洒脱。同时在节奏形态上也不能照搬京剧,否则就会出现地方戏京剧化的倾向,所以说,方法和技巧的运用借鉴“样板戏”也不能过于机械。在此后导演粤剧《野金菊》时,做案头的过程中,我就用了相当一段时间先熟悉广东粤剧的音乐和唱腔,以及其与粤剧表演性格的协调关系,尽量灵活运用不硬套死抠,这出戏的音乐和唱腔设计卜灿荣老师和主演欧凯明、梁淑卿都觉得戏比较灵动,表演发挥得很舒服,舞台呈现很有粤剧特色。至于在主题音乐和人物特性音调等方面的运用上,那难度就更大了,导演和音乐设计者一定要在整体把握和深入开掘上下大功夫,才能在直觉和理性共融中找到合适准确、能让人意会领悟的形象表达方式。
与此同时,在演员演唱的处理上,“样板戏”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比如润腔,就总结了“音色型”“力度型”“装饰型”“节奏型”等方法,这不仅对于创腔者,对于导演也是有意义的。我排戏抠演员的表演时,抠唱就是一项重要的任务,通过抠唱让演员接近人物,接近人物的内心,丰富人物的心理层次。不仅如此,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帮助演员展示自己的演唱技巧。戏曲观众看戏还是要听演唱的功夫技巧,这一点无须回避,这也是戏曲审美的一个重要特点。记得早年间看京剧杨宝森先生的《捉放曹》,曹操误杀吕伯奢一家匆忙离去,路遇吕伯奢沽酒回来,陈宫的一段反西皮散板:“陈宫心中似刀扎,多蒙老丈美意大,好意反成恶冤家,一时间难说你我的真心话,你莫怨我陈宫要怨他。”虽然唱词一般,但是行腔流畅,似断又连,拖腔婉转,音色凄楚,力度收放柔韧,把陈宫心中那种纷乱、欲言又止、无言以对的心情和神态表现得是那么凄凉真切,那么出神入化。每每到此都会赢得满堂彩,在这一瞬间,似乎已经分不清哪是人物哪是技巧了。
在导演专业念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短剧课,实际就是学习京剧的折子戏。早上的基功课是由王艳芳老师把着手教,教戏的老师是当时中国戏曲学校老八年级的刘沪生老师、苏移老师、逯兴才老师和涂沛老师。他们都是名师之后,戏教得好,《打渔杀家》《调寇审潘》《战樊城》《扫松》《贺后骂殿》《打棍出箱》等,说得都非常细致。刘沪生老师是雷喜福先生的学生,逯兴才老师是麒派弟子,涂沛老师宗程派,用戏班子里的话说,肚子里都非常宽敞。老师们教戏的同时也讲了很多戏里的典故和知识,比如,《长坂坡》中“抓披”要领,打把子时脚下的功夫,老先生们演唱时如何耍着板唱,杨小楼先生唱《拜山》里“保镖路过马栏关”时音调似黄不黄的妙处等,这些对我后来的排戏,特别是抠唱都给了很多启示和教益。戏曲现代戏的唱腔虽然是音乐家设计出来的,但它最终的审美效果还是要通过演员演唱的再创造才能赋予生命和灵魂。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唱腔设计者,包括伴奏者和导演一起努力去实现,所以演唱对于戏曲导演来说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艺术手段。我在河北梆子《李保国》的排演中,就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这不仅对演员的情感和内心的呈现起了催化的作用,也强化了全剧的情感冲击力,为观众的审美激情增添了不少宣泄的亮点。
就“样板戏”和后“样板戏”时期的创作而言,总的来说,除去音乐方面的创新外,更多的还是在戏曲现代戏的外在形态上做出了许多探索,为我们积累了许多实践性的成果。但在审美追求上基本上还是以“写实”为主要倾向,这一点在舞台美术上表现得更为突出,那时的天幕形象主要是靠幻灯。在“五七干校”时,我曾被借调到天津地区京剧团一段时间,当时剧团都是学演“样板戏”,没有创作任务,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和中央戏剧学院的卢老师学习画变形格幻灯片,形象都是写实的,据说打幻灯还是从朝鲜学的,这方面他们做得好。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大家对戏曲现代戏的戏曲化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避免“话剧加唱”,强化戏曲身段动作的运用,更要在诗化和意象方面深化实践。这一段时间,我因为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和《中国戏曲通论》的编撰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接触导演实践,但在工作中深受张庚先生、郭汉城先生以及黄克保、何为、龚和德、沈达人等诸位老师的教诲,特别是张庚先生对戏剧导演的实践和论识,以及“剧诗”的学术思想,对我后来的创作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90年代后期,我又开始接触戏曲创作实践,起初更多是一些古装戏,后来又慢慢开始接触现代戏的创作。比如豫剧《老子儿子弦子》《村官李天成》《蓝花碗金豆子》等,我参加这些剧目的创作大多是受当地的领导或是学生相约,以艺术指导的身份来参加具体创作的。《村官李天成》就是一出曾经搬上舞台演出过的剧目,由于领导的关注,要重新修改重排。当时领导抓的力度很大,调集了全省的优秀创作力量,请了姚金城、张芳、韩尔德三位剧作家参与剧本的创作,导演由我的学生张平担任,赵国安任唱腔设计,薛殿杰任舞美设计,贾文龙、汪荃珍主演。在这出戏的演出中,有这样一个场面:李天成带领村民致富的过程中,由于考虑不周,造成了贫富差距,甚至忽略了身边最亲近的老根叔,致使这一位年迈的老人为供养自己的孙女上学,不得不拖着病躯去黄河边卖苦力拉砖挣钱。当李天成看到老根叔拉断了袢绳摔倒在地的情景时,压抑不住自己的自责之情,有一段非常动人的唱:“今日事一桩桩刺疼了我,见袢绳隐隐血痕我忍不住热泪落,多少年多少代拉车走过,多少脚印多少血汗流进了千年黄河,我也曾是黄河岸边的拉车汉,袢绳下肩拉着沉重的生活,重载爬陡坡,路难深深辙,袢绳勒入肉,一挣如刀子割,种一把收一捧只挡住饥饿,拉走了冬拉过了夏,艰辛岁月……”我看到这段唱后,建议伴随着唱一定要给李天成加上一段拉车的身段动作:舞台上的李天成带着深深的自责,拉着重重的一车砖,咬着牙走在那沟沟坎坎的河滩上,哪里难走他走哪里。这段经过特别提炼设计的拉车舞,以生活中拉车上坡下坡的基本动作为依据,加上了传统的程式动作,李天成时而跪搓、时而摔叉、时而吊毛,以此来惩罚自己的失职、发泄自己痛彻心扉的难过。演员边舞边唱,舞蹈的动作节奏和唱腔音乐的旋律交融配合产生了很好的演出效果,成为全剧的一个华彩段落。我常想,有时为了给演员的表演增加一些身段动作,往往要着意设计一些下雨、下雪、行路、追人的场景,以借题发挥,来增加演出的戏曲化特点。这样做未尝不可,但如果我们能把这些身段动作和人物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紧密结合起来,可能在使用和表现上会更有张力。这又让我想起张平导演的豫剧《焦裕禄》,其中有一个类似“滚堂”的身段动作的处理,这个动作如果是安排在焦裕禄肝痛难忍,或是被大风吹得站不住而倒地时完全是合理的。但导演没有这么安排,而是做了更有心机的经营:焦裕禄在治沙的过程中,看到老百姓因饥饿一个个倒下去时,他不得已违反国家统购统销的政策购买了议价粮。此事被上级发现后与他谈话,让他接受严肃处理。这时的焦裕禄内心复杂悸动,引发肝痛难忍,一阵狂风吹来,瘦弱的身躯似乎承受不了这一切,但是他还是挣扎着站了起来,此时这个“滚堂”可就不同一般了,这个身段动作不仅有了物理的、生理的支撑,更有了心理上的动因和自我搏斗的精神力度。
通过这些排演实例,我也在想,这些场面的设计和处理,大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写实性很强,但写实性很强的手法和处理就一定不能写意吗?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应该说非常写实了,那枯黑干瘦的脸上布满了沟壑般的皱纹,干裂的嘴唇,仅剩的一颗门牙,如爬犁般的大手端着破旧的粗瓷碗,那渗出毛孔的汗珠……使人黯然神伤。唯其如此,才让我们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才唤起了我们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情感和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无尽思考!还有北京人艺的现实主义经典剧目《茶馆》,其中王利发、秦二爷、常四爷三位老人撒纸钱为自己送终的场面,不也是极具人生况味和诗性的吗?戏曲何尝不是如此,特别是表现现代生活的戏曲现代戏,怎么能完全避免实具的动作和场景呢!
至于诗化和意象的问题,在我接触的戏曲现代戏排演中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实例。不过,在参加吕剧《海殇》的创作时却碰到过类似的情况。这个剧本是剧作家王勇的手笔,后来因为排演中要不断修改,于是又请烟台吕剧院王明月先生和武汉习志淦先生加盟了编剧。导演是我和我的学生李杰,舞美是薛殿杰老师,灯光是伊天夫老师,作曲是高赴亮老师。这个戏是以中日甲午海战为背景,以北洋水师眷属在这场海战中的不同遭遇为脉络,演绎出的一场“不可重复的民族悲剧”,一个“不可忘记的历史记忆”。剧中写了逃兵管带方伯谦为人所不齿,最后走上断头台的耻辱经历和心理过程,同时写了三位管带夫人虽各自遭遇不同,但她们在悲痛中仍心系大海,与北洋水师共命运的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在甲午海战题材的戏剧中,这出戏的切入点和开掘很独特,知耻而后勇的感召力很是令人振奋!剧本中不乏奇思妙想、神来之笔,比如当方伯谦走上刑场即将被处死之际,他的夫人带着他们的儿子海娃来送行,儿子端上了断头酒,方伯谦双手捧着喝了一口却喷口而吐,原来儿子端上的是海水,方夫人沉痛激动地说:“这就是养育咱见证咱相知相恋的海水,它曾经给我们欢乐给我们梦想,也给了我们失望和悲伤,这海水,致远舰邓世昌邓管带喝过,扬威舰林履中林管带喝过,超勇舰黄建勋黄管带喝过,经远舰林永升林管带喝过,北洋水师多少将士都喝过,你!……”在方夫人的激励下方伯谦终于端起碗来咽下了这碗苦水,含泪说道:“苦啊、咸啊、涩啊……再来,再来!”紧接着起伴唱,方夫人唱“黄海水就是一瓢油,烫滚滚滚烫烫,浇在心里断肝肠;黄海水就是一片心,惊涛骇浪跳动在中国人胸膛;黄海潮啊黄海浪,只盼着后辈儿孙再不把这又咸又苦又涩的海水尝”。高亢而又悲凉的拖腔中,方夫人和海娃也举起盛满海水的大碗一饮而尽!在这动人的场面里有诗情,有理性,也有意象。这出戏的尾声“蹈海”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人打上了刘公岛,几位管带夫人相互搀扶着跪在地上为北洋水师祭礼,当村民们告知几位管带夫人,倭鬼子打过来了,赶快躲一躲吧!她们没有惊慌,只是站起来淡淡地说:“这是咱们的家呀!”然后整装,向海边的礁石走去,相互依靠着坐下来,望着远远的大海,雕像般凝住!我在处理这段戏时,用了钢琴来伴奏,此间听不到炮火声,只有炮火爆炸升起的火焰像节日焰火一样在无声中起起落落,北洋水师的士兵们举着刀枪冲向前又无声倒下,接下来在钢琴伴奏声中响起主题曲儿歌:“山花花,地花花,比不过大海的白浪花,浪花洗脚丫,赶海找婆家,婆家那个他呀,风里浪里走天下,走天下。”钢琴曲继续,舞台是静静的,只有海娃在用望远镜远远地望着,望着……
尾声这般处理,并不在我事先的构思里,而是戏一场一场地排下来,排到这里后突然想到的。没有理性的思考,没有理由,只是直觉,只是直觉里出现的形象,好像是有一点浪漫的感觉,让我说为什么?我说不出来。让我说想表现什么?我也说不出来。我只希望此处能产生一种弥漫整个剧场的气氛,使观众进入一种无以言表的心情与思绪,默默地走出剧场,在目迷五色和喧闹的城市气氛中再苏醒过来。这一仗我们输了,下一仗呢?这或许就是有些人说的“意会思维”吧?创作者无言以表,观看者无言以对,只能意会,难以言传,所以说“意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辞海》)。请原谅我跑题了,谈戏曲现代戏,却跑到了近代故事戏中去了,一方面是因为这出戏的例子具有某种普遍性,另外一点是我对这出戏还真是有点怀念。这出戏的剧本曾获得过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本奖,但在参加地方戏展演时却被告知,有专家说写甲午战争这个题材,必须写邓世昌,不写邓世昌是不行的,于是这出戏就像甲午海战中的沉船一样永沉海底了。
在参加《海殇》的创作之后,我还参与了赣剧《等你一百年》和黄梅戏《英子》的创作,这两部戏的剧本都出自王勇的笔下,导演都是韩剑英。诗化是王勇作品的特点,尤其在这两部作品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剧作本身就各是一首抒情诗。《等你一百年》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讲述一对红军夫妻新婚之日便分手告别了,男人临行前对妻子杜鹃说“等着我”,于是“等待丈夫回来”就成为她生命中的全部。她凭着对革命的信念,对爱情的坚贞等待着,她的梦、她的记忆乃至生命状态,都在等待中度过。戏的结尾处,杜鹃把不断为丈夫编织的草鞋从家里一双一双一直摆到了村口……她站在那里像一座雕像般远望着,等待着,企盼着……戏里没有什么口号,在戏画上了句号以后,我在这里增加了一个处理,一队脚穿草鞋身背斗笠和大刀的红军,从剧场的太平门走来,列队站在乐池前,在一声“敬礼”的庄严喊声中,全体战士举手向这位伟大的红军战士的妻子杜鹃致军礼!然后又转身向观众敬礼!意在要把“诗”中浓郁的个人情感提升为崇高的精神。
黄梅戏《英子》,写一位红军女战士英子在西征时遭马匪围剿英勇跳崖,被藏族青年桑杰搭救,多次寻找队伍未果,只好留在了雪域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经身为解放军首长的英子的丈夫,来到藏区寻找妻子,两人面对面似乎已经相识,但英子认为自己没有保护好她与丈夫唯一的孩子,又与搭救她的藏族青年生活在一起了,深感自责,一直不承认自己是英子,她对丈夫说“雨神流走了她的容颜,风神吹走了她的年华,苍鹰带走了她的灵魂……她死了”,始终没有与丈夫相认。丈夫理解她的心情,默默离去,这时她望着丈夫离去的背影有一段唱,“远去了,已不见人影,耳边还回旋马蹄声,盼这天早来临,怕这天两相逢,英子早不是当年的英子,青海湖畔负旧情。英子也不是当年的战士,脱离红军雁独行,我不是好妻子,也不是好母亲,更不是好女人,只有心还是当年那颗心,还有不变的真诚,让真诚留在浪花里,让纯洁飘在雪花中”。伴唱起:“爱人把心给了我……一样的心跳一样的脉搏。”我在这里特别强调,要让无奈又无助的英子望着她丈夫远去的背影,举起颤抖着的手敬一个真诚而凝重的军礼!诗有时是柔弱的、是悲情的,这往往就需要我们把诗背后的灵魂和精神提升出来,让人们在浓郁感人的诗情中感受到深深埋藏的理性精神的闪光!在戏的结尾时,80多岁的英子对桑杰说:“桑杰呀!多年之后别忘了在我墓碑上写上:红军女战士——英子。”前后对照,这是多么重要的一笔呀!有时候细节真的是不可疏忽的。
另外还有一点体会,诗化也好意象也好,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剧”字,戏曲在形态上虽然是歌舞化的,但其本质仍然是戏剧,所以张庚先生对戏曲的诗性用的是“剧诗”来概括,其中剧是前提,那么意象呢,自然也应该是戏剧的意象。是戏剧自然就要敷演故事,敷演故事自然就要有情节,自然就要有人物和表现人物的行为动作,还要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正因为如此,戏曲的表演就一定会有描摹人物行为动作的写实成分。特别是现代戏,虽然经过了艺术的提炼和加工,但其仍然不失生活的来源,因而戏曲的歌舞化是一个很宽泛的表现,是在接近生活形态的程式动作和歌舞程式两极之间的地带中滑动的。可以认为传统戏的歌是从念白到歌唱的不同层面的阶梯式攀升,其中有最接近生活的方言白,还有半韵白、韵白等直到歌唱;舞蹈化的身段动作也是如此,既有最接近生活原型的程式,如行走、开门关门、做针线活、喂鸡喂鸭等,又有“起霸”“走边”和完全歌舞形态的程式,如《霸王别姬》中的剑舞,《牡丹亭》中的“堆花”类的群舞。唯其如此,才能既表现人物的行为动作又能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抒发人物的情感,表现更深刻的思想,所以戏曲才能是戏剧。如果离开了这一前提,“诗化”也好“意象”也好,就会变得空泛了。
再者,戏曲的“诗化”和“意象”大多是在戏剧动态中营造出来的,如果拉开大幕就出现一个意象符号,可能观众会很难理解,只有随着剧情的发展人们才会渐渐看懂它的意思,我们写文章能把这一符号解释得很明白,那是在看完全剧以后才有的认识。诗化也是如此,诗化当然与文学语言有关,但戏剧的诗化不仅与文学语言有关,还与整个综合体的方方面面有关,常常与灯光、布景、音乐的介入有关,与戏剧情节的流动有关。所以我前面说的,大幕没有拉开的时候主题曲的前奏很难捕捉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我们创作者是明白的,但观众就不一定清楚了,在戏的进行中,主题旋律作为主导动机不断被使用后,其背后的意蕴才会逐渐显示出来。记得我初次接触著名的山水画《富春山居图》时,为了看懂它,就翻了一些关于这幅画的解读文章,其中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的文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讲述了这幅画背后的文化意象,他说:“山水审美是什么呢?是文人的心灵与山水的碰撞。”在这幅画里,黄公望“把山水当作身体与心灵栖居的田园,当作一种哲学,当作能够让生命得到安顿的精神圣地,这是《富春山居图》所传递的一个重要意象”[1]。但是,当我再看这幅著名的画作时却还是找不到这样的认识。于是又请教专家,专家说,“不要仅仅局限于画面本身,先给你讲讲故事”,于是专家非常详细地讲述了黄公望充满戏剧性的一生和他的人生心路,然后让我再去读画。果然,当我再去一段一段读这幅“散点透视”的7米长卷时,确实就有了一些更加丰富的感悟和认知。由此也可以说明,戏剧舞台上的“诗化”和“意象”都离不开戏剧性的营造,这营造一是需要戏剧情节的写实铺垫,人物内心能量的铺垫;二是要有整体把握,时间的、空间的整体把握,观众连戏都没看明白,或是还没看到戏剧情节的进展是很难理解意象背后的意蕴,并被诗化场面感动的。戏剧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前后关系”,前后关系的处理真的会产生伟大的戏剧效果。当然,局部一段充满诗意的唱词加上很好的演唱表达,再加上很美的伴舞也会有动人的诗意,但总不如进入更深入、更整体的精神或意蕴层面更有意味和审美价值。
我在导演河北梆子《李保国》时,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李保国因劳累心脏病复发,病情严重只能住院治疗,可正在这关键时刻他帮扶的地方突然发生倒春寒,亟须他的指导救援,虽然李保国的夫人极力拦阻,但李保国还是不顾疾病带来的危险出发了。本来我计划要在这里安排一段舞蹈化的场面,在钢琴曲《命运》主旋律的伴奏下,李保国走翻扑滚跌的身段,为适应钢琴伴奏的风格,身段走“京武体三结合”的路子,力求让这一设计成为刻画李保国精神高度的华彩段落,成为戏剧情节和情境发展的必然。但是几经实验排练都没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事后思考和分析,一方面是表演的难度,另一方面也是戏剧经营的问题。在之前的戏剧铺陈里,人物内心世界的张力还没铺垫到位,戏剧情势的能量还没有累积到可以“尖端放电”的那一刻。另外,有人说,虚从实中来,意在虚中含,有意化为象,虚实相互生。戏剧的意象是创作主体跟观众对话与交流的一个重要支点,是为了让观众去领悟那更深刻、更宽泛的言外之意,不是你自己完全的主观抒发,所以戏剧的意象是一种“意会思维”,是你和观众之间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默契。
近些年来,戏曲导演的职能和创造力有了非常明显的强化,虽然不像电影创作那样,导演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戏曲导演在一、二度创作中的统筹地位也显得更加突出了。另外戏剧观念的多元化,叙事结构的多样化,舞台手段的日益丰富和现代化、科技化,都在使戏曲导演创作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随着创作题材的不断丰富,特别是对题材开掘的角度的丰富和不断深化,现时的戏曲对导演的生活积累、思想深度、文化素养、审美水平等诸方面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在导演进修班讲课的时候曾说过,决定导演水平的因素是在导演之外!
(黄在敏,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原载《戏曲研究》第123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注释】
[1] 胡晓明《〈富春山剧图〉背后的文化意象》,《解放日报》2021年7月16日第7版。
微信公众号: 戏曲研究
温馨提示:内容来源于网络,仅用于学习交流参考,无商业用途,如有不妥请联系本站,将立即删除!
郑州戏曲学校是河南省专业的豫剧中专学校,也是郑州市唯一学历教育戏曲中专学校,开设有3/5年制大专、中专班,欢迎报考!